想象力的创造力……文化和艺术,此时开始得到我们如今的意义。2. 如果你有志于阅读拜伦的诗、歌德的《浮士德》、卢梭的《忏悔录》,或者希望了解贝多芬、李斯特、帕格尼尼、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涵,这本书一定不容错过。本书另附16页全彩插图,配合书中内容展示了浪漫主义时代的代表性绘画和建筑。3. 关于“浪漫”和“浪漫主义”,我们已经听了太多肤浅、庸俗的说法,《浪漫主义革命》将正本清源,讲讲“浪漫”的渊源与真谛。4. “新思•观察家精选”系列之3。“新思•观察家精选”汇集具有当代回声的历史话题,旨在帮助我们收整见识的碎片,读懂现代世界的由来,反思现代人的生活境况。书的篇幅都在200至300页之间,外形精巧;这些*作者所讲述的既是各自*擅长的话题,也是同一个大时代的不同投影。希望你通过了解永不止步的时代变迁,增长对未来的远见。【内容简介】《浪漫主义革命》为你带来18、19世纪间的一段别开生面的欧洲历史和艺术史。这是关于“浪漫”的*初的故事。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用理性、科学为人类社会勾画了一幅宏伟蓝图;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的社会是冰冷的——用科学公式贬低了人的灵魂,用理性和功


 亚美尼亚人屠杀称为“基督徒和@之间数千次斗争中的一桩”。然而如同本书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较大多数国家更能容纳语言和@的差异。对于曾目击奥斯曼末日的汤因比而言,冲突的来源显然在这个区域之外。他于1922年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种族净化”——不论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亚,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发性爆发,而是宪兵和军队故意以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平民。它代表着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打破社会结构所必需的极端力量,若是没有这一力量社会本可以忽视阶级和种族的裂痕。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看法。有位奥地利读者看过我在1994年写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内幕》,说我对于德军20世纪40年代在巴尔干的行径下了过于严厉的断言。依他之见,最近的冲突事件再度证明了巴尔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倾向。而我认为,从茂特豪森的战时奴隶劳动营即可看出
亚美尼亚人屠杀称为“基督徒和@之间数千次斗争中的一桩”。然而如同本书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较大多数国家更能容纳语言和@的差异。对于曾目击奥斯曼末日的汤因比而言,冲突的来源显然在这个区域之外。他于1922年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种族净化”——不论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亚,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发性爆发,而是宪兵和军队故意以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平民。它代表着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打破社会结构所必需的极端力量,若是没有这一力量社会本可以忽视阶级和种族的裂痕。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看法。有位奥地利读者看过我在1994年写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内幕》,说我对于德军20世纪40年代在巴尔干的行径下了过于严厉的断言。依他之见,最近的冲突事件再度证明了巴尔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倾向。而我认为,从茂特豪森的战时奴隶劳动营即可看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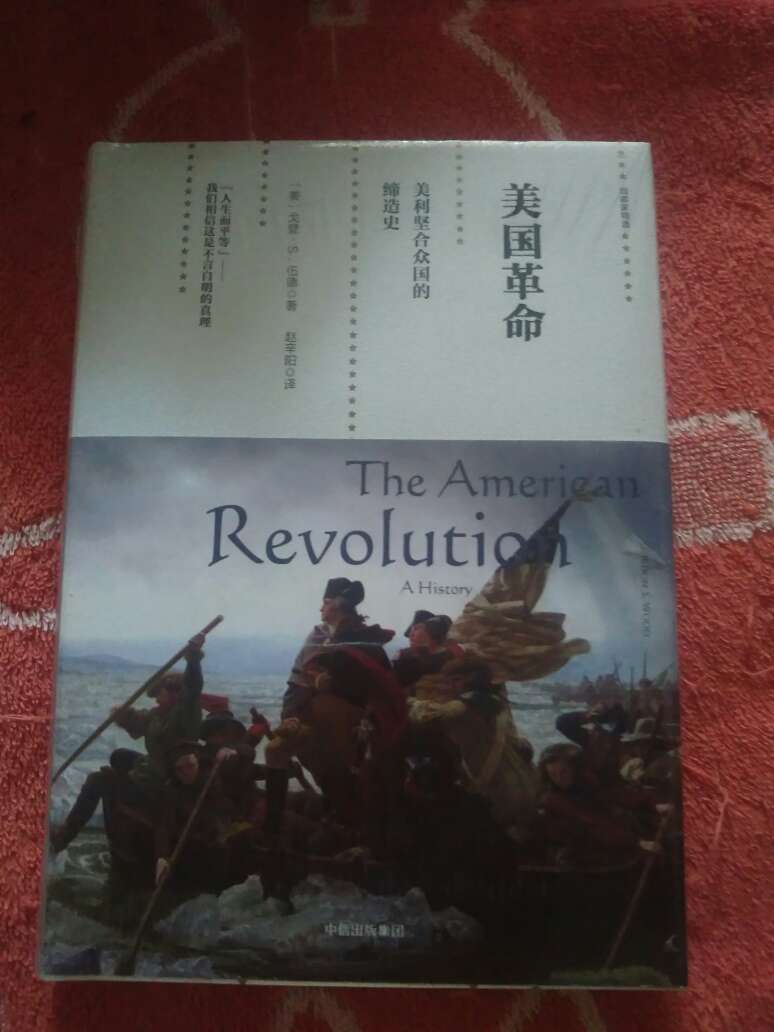 西班牙全境终于“光复”。几乎是在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贵族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信仰。持续五百年的@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他们一旦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坚毅性、狂热性,以及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是1000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后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学会了航海。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时他们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贸易的大门;到了15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伽
西班牙全境终于“光复”。几乎是在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贵族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信仰。持续五百年的@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他们一旦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坚毅性、狂热性,以及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是1000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后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学会了航海。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时他们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贸易的大门;到了15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