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


 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
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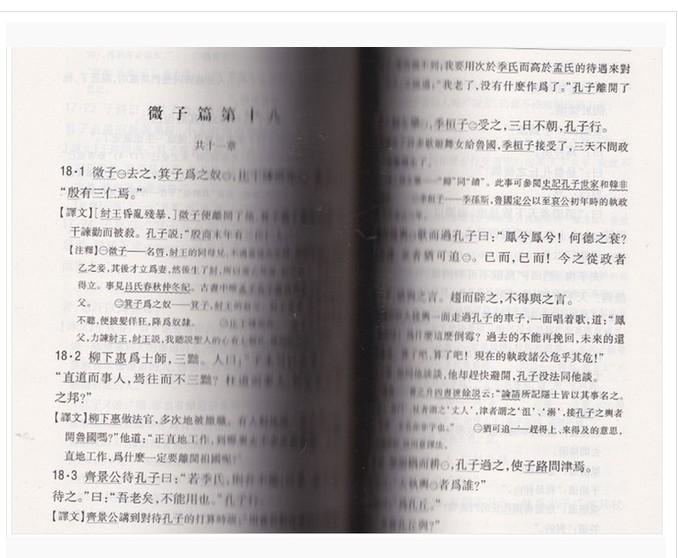 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
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