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r“那,不分不就行了!”r“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r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30,她就26岁了。较之前路上将面临的物的规模,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4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r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r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r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r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r7月24日,上午8时25分r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
 “有兴趣。耳朵实在漂亮无比。”r“那倒是,耳朵的确是的。”摄影师支支**地说,“不过人倒不见得怎么样。要是想和年轻女孩约会,把最近拍摄泳装的模特介绍给你好了。”r“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r2点、6点、10点给她打了3次电话,都没人接。看来她也以她的方式活得很忙。r好歹逮住她已是翌晨10点了。我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想就前几天广告上的事稍微谈谈,提议一起吃晚饭如何。r“听说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r“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说。r她似乎有点惶惑,但没再问什么。我们讲定明天傍晚在青山大街一家咖啡馆碰头。r我给以前去过的餐馆中最为高级的法国风味店打电话预订桌子。然后拿出一件新衬衫,花时间挑选领带,穿上只上过两次身的外衣。r如摄影师好意告诉的那样,她确实是个不甚起眼的女孩。衣着长相都稀松平常,俨然二流女子大学合唱队里的。当然,对我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失望的是她把耳朵严严实实藏在了梳成流线型的头发里。r“耳朵藏起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说。r“嗯。”她也若无其事地应道。r由于比约定时间到得早,我们成了晚餐时间的第一
“有兴趣。耳朵实在漂亮无比。”r“那倒是,耳朵的确是的。”摄影师支支**地说,“不过人倒不见得怎么样。要是想和年轻女孩约会,把最近拍摄泳装的模特介绍给你好了。”r“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r2点、6点、10点给她打了3次电话,都没人接。看来她也以她的方式活得很忙。r好歹逮住她已是翌晨10点了。我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想就前几天广告上的事稍微谈谈,提议一起吃晚饭如何。r“听说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r“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说。r她似乎有点惶惑,但没再问什么。我们讲定明天傍晚在青山大街一家咖啡馆碰头。r我给以前去过的餐馆中最为高级的法国风味店打电话预订桌子。然后拿出一件新衬衫,花时间挑选领带,穿上只上过两次身的外衣。r如摄影师好意告诉的那样,她确实是个不甚起眼的女孩。衣着长相都稀松平常,俨然二流女子大学合唱队里的。当然,对我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失望的是她把耳朵严严实实藏在了梳成流线型的头发里。r“耳朵藏起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说。r“嗯。”她也若无其事地应道。r由于比约定时间到得早,我们成了晚餐时间的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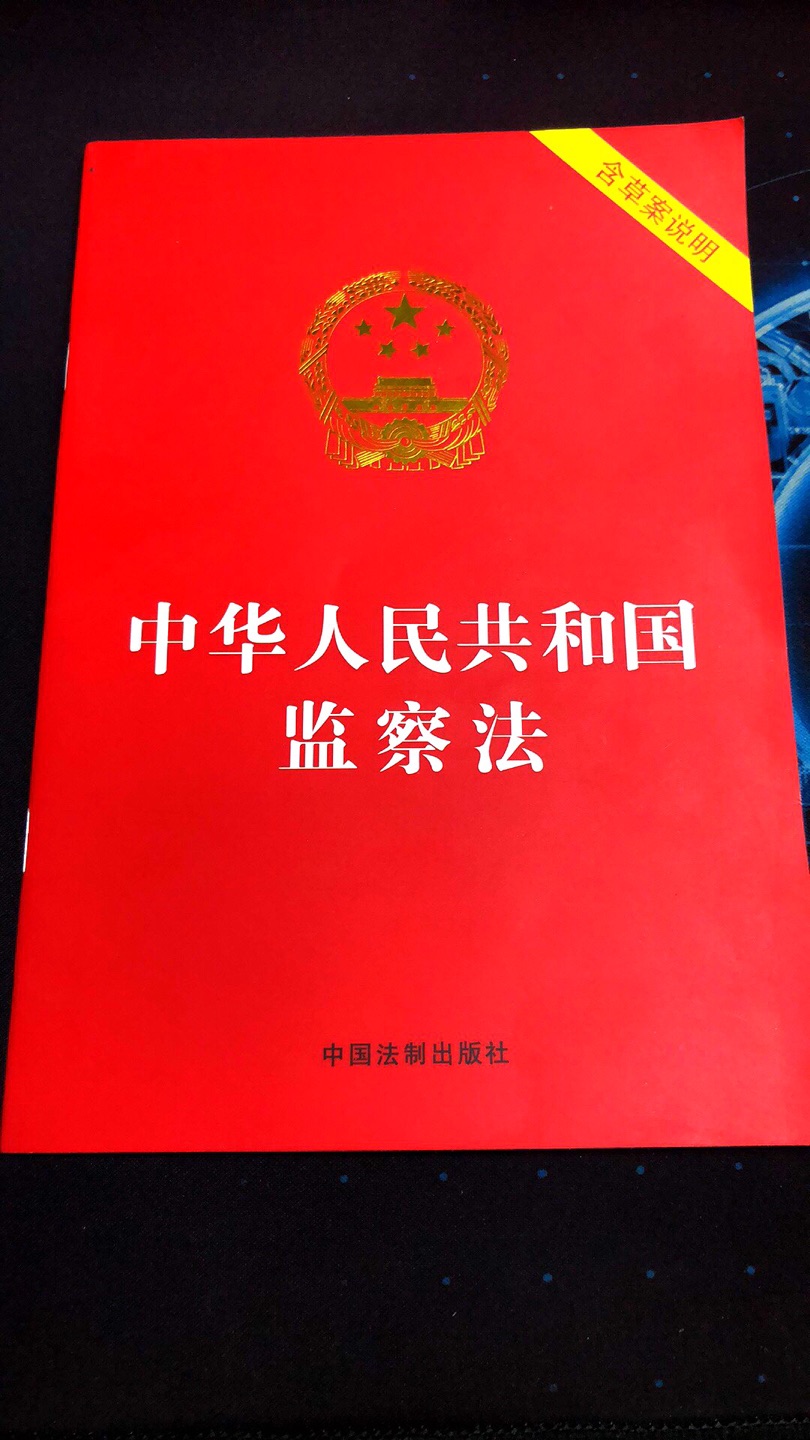 凑单学,才是真的学。
凑单学,才是真的学。


 “有兴趣。耳朵实在漂亮无比。”r“那倒是,耳朵的确是的。”摄影师支支**地说,“不过人倒不见得怎么样。要是想和年轻女孩约会,把最近拍摄泳装的模特介绍给你好了。”r“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r2点、6点、10点给她打了3次电话,都没人接。看来她也以她的方式活得很忙。r好歹逮住她已是翌晨10点了。我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想就前几天广告上的事稍微谈谈,提议一起吃晚饭如何。r“听说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r“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说。r她似乎有点惶惑,但没再问什么。我们讲定明天傍晚在青山大街一家咖啡馆碰头。r我给以前去过的餐馆中最为高级的法国风味店打电话预订桌子。然后拿出一件新衬衫,花时间挑选领带,穿上只上过两次身的外衣。r如摄影师好意告诉的那样,她确实是个不甚起眼的女孩。衣着长相都稀松平常,俨然二流女子大学合唱队里的。当然,对我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失望的是她把耳朵严严实实藏在了梳成流线型的头发里。r“耳朵藏起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说。r“嗯。”她也若无其事地应道。r由于比约定时间到得早,我们成了晚餐时间的第一
“有兴趣。耳朵实在漂亮无比。”r“那倒是,耳朵的确是的。”摄影师支支**地说,“不过人倒不见得怎么样。要是想和年轻女孩约会,把最近拍摄泳装的模特介绍给你好了。”r“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r2点、6点、10点给她打了3次电话,都没人接。看来她也以她的方式活得很忙。r好歹逮住她已是翌晨10点了。我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想就前几天广告上的事稍微谈谈,提议一起吃晚饭如何。r“听说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r“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说。r她似乎有点惶惑,但没再问什么。我们讲定明天傍晚在青山大街一家咖啡馆碰头。r我给以前去过的餐馆中最为高级的法国风味店打电话预订桌子。然后拿出一件新衬衫,花时间挑选领带,穿上只上过两次身的外衣。r如摄影师好意告诉的那样,她确实是个不甚起眼的女孩。衣着长相都稀松平常,俨然二流女子大学合唱队里的。当然,对我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失望的是她把耳朵严严实实藏在了梳成流线型的头发里。r“耳朵藏起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说。r“嗯。”她也若无其事地应道。r由于比约定时间到得早,我们成了晚餐时间的第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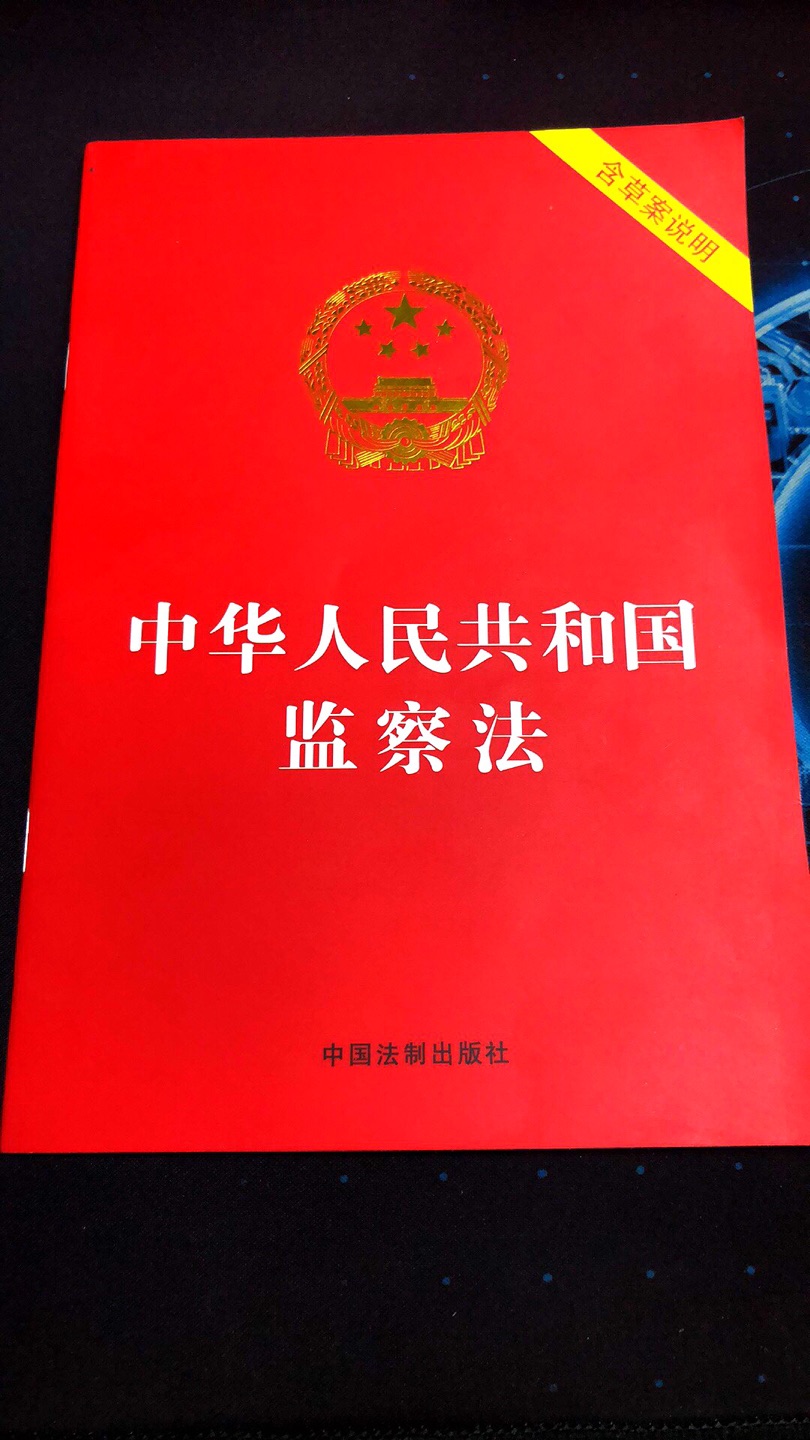 凑单学,才是真的学。
凑单学,才是真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