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亦真亦幻的文本和历史里,萨福的一生充满传奇。她有时容颜美艳、绮丽非凡,有时是以诗才震撼柏拉图、奥维德和薄伽丘的世间奇女子。柏拉图曾称萨福为第十位文艺女神。奥维德曾写下《萨福致法翁》,“我不能不调整我的竖琴,让它适应我的眼泪。”以这样悲伤的诗句,阐述萨福对一个名叫法翁的自由而不肯停留的精灵水手的无望爱情。薄伽丘在《列女传》中也哀叹道:“她在诗艺中得到的幸福,一如她在爱情中遭遇到的不幸:爱上一个青年男子,为了他的魅力,或者美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屈服于难以忍受的折磨。他拒绝服从她的欲望,于是,悲伤的萨福写出哀悼的诗篇……我们是不是应该责备缪斯女神呢?当安菲翁弹唱诗歌的时候,她们肯为他移动奥吉及亚的石头,却不肯为萨福移动那位年轻男子的心。” 但也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在洪钟大吕一样的女人尤瑟纳尔眼中,萨福不是弹奏着竖琴歌咏爱情的女诗人,只是“一个走钢丝的杂技艺人”。她甚至“形象苍白,乳房萎缩,像死亡或是麻风病人。” 是爱与美神的代言人,还是病态的民间女子;死于心碎,死于爱情,还是死于自然的生命终结;那些断编残简的诗句,是属于某种集体的智慧,还是一个叫“萨福”的女诗人的结晶。这些都有了疑虑,甚至要变成诠释者过度诠释的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达得理 费茨曾说,“人们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关于萨福的事情,而我们却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也许萨福这个浪漫传奇,只是世人营造以娱人娱己的浪漫神话而已。也许又不是。这猜测将跟随岁月长久地持续下去,但这关乎世人自身的情怀,已无关速朽的躯体和不会消逝的诗。 在某个版本的历史里,萨福是一个类似于学校的女子团体的灵魂人物。她常带领她的介乎朋友和女弟子般的女孩儿们,唱歌、祭祀,弹琴、跳舞。 “在春天的薄暮 在满月盈盈的光辉下 女孩子们聚在一起 …………… 用温柔的脚步 在开花的柔滑的草地上 围绕着爱的祭坛. 跳起环舞” 萨福的诗并不是我最喜爱的那种诗的类型。也许在这个时期,那些孤独气质,开阔视界,痛苦和辛辣交织,具有深邃而绵密的纹理的诗更能打动我。但人总不能在一种状态之下沉浸太久,就像你在幽蓝的海底蛰伏,濒临缺氧之际,偶尔也需要浮出水面透一口气。读萨福,或许就如你刚浮上水面的那一刻——彼时,晴空万里,阳光直射入海面,你的心如同这碧蓝的海水,一切似乎都美好、质朴而明净。 萨福的女孩儿们,有着“粉红色的足踝”,或“蔷薇色的手臂”,还有眼神,“温柔如蜜”。 爱总是在魔鬼身上,也能看见天使般的微光。无论此间的女同性恋的传闻是否属实,萨福爱她们,爱那些女孩儿们。是爱,而不是别的什么,让她在谁家的女孩子身上都能看到的骄纵的性情脾气或许偶尔粗陋的言行之外,看到温柔和甜蜜。 喔,“她如此温柔 她快要 杀死我了,用 爱——” 美好,曾如星空般明净开阔,曾如不舍昼夜的河流。但萨福也有她的污秽凄苦。在诗集的第五辑(或者从第四辑开始),萨福也渐露疲惫和倦怠。 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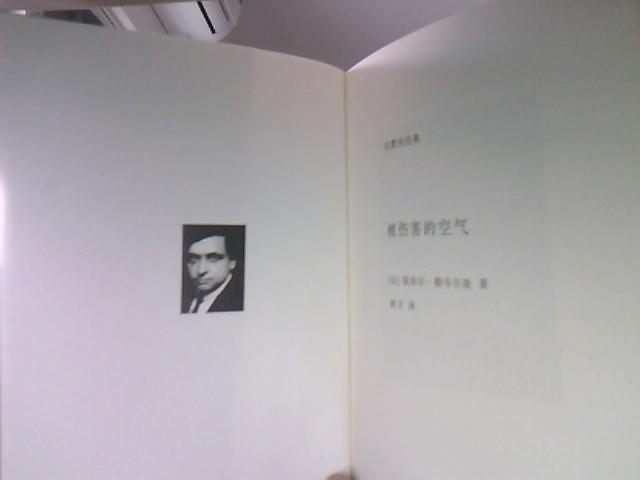

 恩,很好的一本书,值得拥有
恩,很好的一本书,值得拥有 在那些亦真亦幻的文本和历史里,萨福的一生充满传奇。她有时容颜美艳、绮丽非凡,有时是以诗才震撼柏拉图、奥维德和薄伽丘的世间奇女子。柏拉图曾称萨福为第十位文艺女神。奥维德曾写下《萨福致法翁》,“我不能不调整我的竖琴,让它适应我的眼泪。”以这样悲伤的诗句,阐述萨福对一个名叫法翁的自由而不肯停留的精灵水手的无望爱情。薄伽丘在《列女传》中也哀叹道:“她在诗艺中得到的幸福,一如她在爱情中遭遇到的不幸:爱上一个青年男子,为了他的魅力,或者美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屈服于难以忍受的折磨。他拒绝服从她的欲望,于是,悲伤的萨福写出哀悼的诗篇……我们是不是应该责备缪斯女神呢?当安菲翁弹唱诗歌的时候,她们肯为他移动奥吉及亚的石头,却不肯为萨福移动那位年轻男子的心。” 但也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在洪钟大吕一样的女人尤瑟纳尔眼中,萨福不是弹奏着竖琴歌咏爱情的女诗人,只是“一个走钢丝的杂技艺人”。她甚至“形象苍白,乳房萎缩,像死亡或是麻风病人。” 是爱与美神的代言人,还是病态的民间女子;死于心碎,死于爱情,还是死于自然的生命终结;那些断编残简的诗句,是属于某种集体的智慧,还是一个叫“萨福”的女诗人的结晶。这些都有了疑虑,甚至要变成诠释者过度诠释的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达得理 费茨曾说,“人们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关于萨福的事情,而我们却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也许萨福这个浪漫传奇,只是世人营造以娱人娱己的浪漫神话而已。也许又不是。这猜测将跟随岁月长久地持续下去,但这关乎世人自身的情怀,已无关速朽的躯体和不会消逝的诗。 在某个版本的历史里,萨福是一个类似于学校的女子团体的灵魂人物。她常带领她的介乎朋友和女弟子般的女孩儿们,唱歌、祭祀,弹琴、跳舞。 “在春天的薄暮 在满月盈盈的光辉下 女孩子们聚在一起 …………… 用温柔的脚步 在开花的柔滑的草地上 围绕着爱的祭坛. 跳起环舞” 萨福的诗并不是我最喜爱的那种诗的类型。也许在这个时期,那些孤独气质,开阔视界,痛苦和辛辣交织,具有深邃而绵密的纹理的诗更能打动我。但人总不能在一种状态之下沉浸太久,就像你在幽蓝的海底蛰伏,濒临缺氧之际,偶尔也需要浮出水面透一口气。读萨福,或许就如你刚浮上水面的那一刻——彼时,晴空万里,阳光直射入海面,你的心如同这碧蓝的海水,一切似乎都美好、质朴而明净。 萨福的女孩儿们,有着“粉红色的足踝”,或“蔷薇色的手臂”,还有眼神,“温柔如蜜”。 爱总是在魔鬼身上,也能看见天使般的微光。无论此间的女同性恋的传闻是否属实,萨福爱她们,爱那些女孩儿们。是爱,而不是别的什么,让她在谁家的女孩子身上都能看到的骄纵的性情脾气或许偶尔粗陋的言行之外,看到温柔和甜蜜。 喔,“她如此温柔 她快要 杀死我了,用 爱——” 美好,曾如星空般明净开阔,曾如不舍昼夜的河流。但萨福也有她的污秽凄苦。在诗集的第五辑(或者从第四辑开始),萨福也渐露疲惫和倦怠。 于是
在那些亦真亦幻的文本和历史里,萨福的一生充满传奇。她有时容颜美艳、绮丽非凡,有时是以诗才震撼柏拉图、奥维德和薄伽丘的世间奇女子。柏拉图曾称萨福为第十位文艺女神。奥维德曾写下《萨福致法翁》,“我不能不调整我的竖琴,让它适应我的眼泪。”以这样悲伤的诗句,阐述萨福对一个名叫法翁的自由而不肯停留的精灵水手的无望爱情。薄伽丘在《列女传》中也哀叹道:“她在诗艺中得到的幸福,一如她在爱情中遭遇到的不幸:爱上一个青年男子,为了他的魅力,或者美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屈服于难以忍受的折磨。他拒绝服从她的欲望,于是,悲伤的萨福写出哀悼的诗篇……我们是不是应该责备缪斯女神呢?当安菲翁弹唱诗歌的时候,她们肯为他移动奥吉及亚的石头,却不肯为萨福移动那位年轻男子的心。” 但也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在洪钟大吕一样的女人尤瑟纳尔眼中,萨福不是弹奏着竖琴歌咏爱情的女诗人,只是“一个走钢丝的杂技艺人”。她甚至“形象苍白,乳房萎缩,像死亡或是麻风病人。” 是爱与美神的代言人,还是病态的民间女子;死于心碎,死于爱情,还是死于自然的生命终结;那些断编残简的诗句,是属于某种集体的智慧,还是一个叫“萨福”的女诗人的结晶。这些都有了疑虑,甚至要变成诠释者过度诠释的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达得理 费茨曾说,“人们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关于萨福的事情,而我们却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也许萨福这个浪漫传奇,只是世人营造以娱人娱己的浪漫神话而已。也许又不是。这猜测将跟随岁月长久地持续下去,但这关乎世人自身的情怀,已无关速朽的躯体和不会消逝的诗。 在某个版本的历史里,萨福是一个类似于学校的女子团体的灵魂人物。她常带领她的介乎朋友和女弟子般的女孩儿们,唱歌、祭祀,弹琴、跳舞。 “在春天的薄暮 在满月盈盈的光辉下 女孩子们聚在一起 …………… 用温柔的脚步 在开花的柔滑的草地上 围绕着爱的祭坛. 跳起环舞” 萨福的诗并不是我最喜爱的那种诗的类型。也许在这个时期,那些孤独气质,开阔视界,痛苦和辛辣交织,具有深邃而绵密的纹理的诗更能打动我。但人总不能在一种状态之下沉浸太久,就像你在幽蓝的海底蛰伏,濒临缺氧之际,偶尔也需要浮出水面透一口气。读萨福,或许就如你刚浮上水面的那一刻——彼时,晴空万里,阳光直射入海面,你的心如同这碧蓝的海水,一切似乎都美好、质朴而明净。 萨福的女孩儿们,有着“粉红色的足踝”,或“蔷薇色的手臂”,还有眼神,“温柔如蜜”。 爱总是在魔鬼身上,也能看见天使般的微光。无论此间的女同性恋的传闻是否属实,萨福爱她们,爱那些女孩儿们。是爱,而不是别的什么,让她在谁家的女孩子身上都能看到的骄纵的性情脾气或许偶尔粗陋的言行之外,看到温柔和甜蜜。 喔,“她如此温柔 她快要 杀死我了,用 爱——” 美好,曾如星空般明净开阔,曾如不舍昼夜的河流。但萨福也有她的污秽凄苦。在诗集的第五辑(或者从第四辑开始),萨福也渐露疲惫和倦怠。 于是